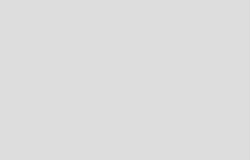最后的农民:四十年前的乡村记忆

►乡下的老屋
前言
四十年前,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。曾经,乡村生活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在简单纯真的生活中,孩子们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,学会了播种、收获、烧柴、拾粪和养鸡喂鸭。工业化农场到来的时候,也是田园牧歌消逝的时候,谁也无法阻止乡村抒怀时代的渐行渐远。传承千年的农业文明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今天仍留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,已然是最后一代农民!
撰文 | 崔凯
责编 | 程莉
● ● ●
中秋之夜,魔都上海皓月当空,读小学的女儿嚷着用手机给月亮拍照。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儿,我的思绪却飘回到自己的少年时光。四十年前,我也在读小学,生活在东北农村,那里有个很荒凉的名字—“孤店子”。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,我出生在这里。
老屋与少年
小时候,整个村里只有五间茅草屋,四周农田环绕,象个孤岛,我曾自喻这里是“小台湾”。村东有一条羊肠小路,小路上有两条车辙印,杂草在中间顽强的生长着。有一次,看到一个画家坐在小路上画这五间茅草屋,后来才知道那叫“写生”。老屋前有条小河,河边原有几棵大柳树。沿着河边,筑起篱笆墙,上面落满了蜻蜓。屋后有一亩大小的菜园,四周种了一圈一米高的榆树墙。老屋只有里外两间,里屋是炕,外屋是灶,屋檐下还曾有过燕子窝。当年我站在窗前向南眺望,可以看到绵延几十里的农田,夏天绿荫荫的,象地毯一样。高天流云给人一种开阔的心境。四月翻地,五月插秧,八月抽穗,九月收割,春华秋实。在田里劳作的有人和黄牛,后来才有了拖拉机。
当年的农村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,孩子都是散养,每天就在外面疯玩。他们在蹒跚学步时就和各家各户的看门狗脸熟,来去畅通无阻。男孩喜欢弹弹珠,打弹弓,抓青蛙,逮蝈蝈,女孩跳橡皮筋、踢键子、打沙包、弹旮旯哈(猪的关节骨)。很多人家都是三、五个孩子,大的不愿意带着小的玩,跑在前面,小的哭着在后面追。在外面闯了小祸,回家挨打、罚跪更是常事。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上小学以后帮父母做家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那时候村东有一口水井,记得我第一次担水是10岁,挑满一缸水要往返三次。每年四月春耕时节,大量机井要抽水灌溉农田,地下水位下降,这口井就会枯水,只能赶到二里路以外的另一口深井去挑水,人多时还得排队。南边篱笆墙下种了一垄齐腰高的忘忧草(俗名黄花菜),一簇簇长得很茂密。盛夏里绿叶上缀满了黄花,金灿灿一片。从小学到大学的暑假,每天清晨母亲都会唤我起来采摘花瓣。摘下来的花瓣先要放在大锅里蒸熟,再一根一根摆在高粱秸秆制成的帘子上晾晒,很是繁琐。遇上晴热的天气,一天就可以晾干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若一场雨下来,就会前功尽弃。
清晨,屋檐下有很多张蜘蛛网,用铁丝做成一个圆环,接在一根竹杆上,很像一支加长的羽毛球拍。在圆环上绕上几层蜘蛛网,跑到菜地里。很多蜻蜓夜里停歇在葱叶尖上,翅膀上甚至还有露珠。拿着蜘蛛网拍悄悄靠近,再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过去,一下可以逮到七八只蜻蜓。当然,更多的蜻蜓都是徒手抓的,每天都能逮到几百只——这可是鸡、鸭的美食,吃蜻蜓下出来的蛋黄都是深红色的。可别小瞧院子里这十几只鸡鸭,那时候的日子粗茶淡饭,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,饭桌上才见得到肉和蛋。小孩子绝不允许上大人的饭桌,在灶台边留着口水。心软的母亲会偷偷留下点锅底,放在孩子饭碗里,让孩子躲在外屋偷吃。
家里还养了十几只兔子,我每天放学回家后,先拿起扁担、镰刀和篮筐去田野里割草。初秋的田埂上草长得很茂盛,一脚踩下去会惊起很多小青蛙。最不喜欢一种名为“剌剌秧“的野草,在田野里匍匐缠绕,刮在皮肤上就是一道血痕。最有趣的事情是淘鱼。村东小路旁有一条一米宽的水渠,找一段草密水浑的河段,两头筑上泥坝,十几岁的男孩,拿着家里的洗脸盆,赤脚光背站在渠道里,挥汗如雨、“涸泽而渔”。收获了满满一盆,大都是一拃长的鲫鱼。欢天喜地地拿回家里,晚饭有鱼吃,父亲也从橱柜里拿出那瓶泡着人参的白酒。
上学了,小学校舍就是两排平房,教室里没有电灯,更没有暖气。冬天,教室里会生火炉子取暖,看着玻璃窗上美丽的窗花渐渐融化。乡下孩子写作业应付了事,很少知道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课外读物只是连环画和小人书。自行车当然是奢侈品,大家都是走路上学,近的一二里,远的有七八里路,路上嬉笑打闹。学校的广播在中午会播放刘兰芳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有的同学中午不回家,带着饭盒,就站在操场上一边吃饭,一边听评书。
那年头,有雨伞的同学也不多,遇到雨天就拿块塑料布披在身上,一路走下来,下半身也都是湿透的。不过也有好玩的时候:秋天是大豆收获的季节,几个同学在放学路上顺手牵羊,从路边的地里拔出几株豆子,围坐在地头,“烤豆燃豆萁“。随着“噼啪”的响声,豆香气很快飘出来。等豆秸快燃尽时,大家七手八脚把火踩灭,开始在草灰中拾拣烤熟的豆粒,吃得嘴巴和手指沾满黑灰,却津津有味。
小学校的南侧有片开阔的空地,姑且算作一个广场。每个月这里都会放映一场露天电影。从来不需要张贴海报,十里八村口口相传,妇孺皆知。夜幕降临时,人们陆续聚集过来。银幕就用绳子系在两根有些歪斜的松木杆上。早来的孩子们已经抢占了前排位置。有时银幕正面坐满了人,后来者就坐到反面去——也只有露天电影才能见到这种幕布两边都有观众的景象。大人们的闲聊与孩子们的嬉闹和在一起,非常热闹。放映员对焦时,不时有人把手伸到光路里,在幕布上映出手型。等到电影放映时,才渐渐静了下去。就是在这个广场里,我看到过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桥》和《大闹天宫》等片子。露天电影毕竟数量有限,更多的影片还是通过广播收听录音剪辑,也就此知道了“邱岳峰、陈述、童自荣”等配音演员的名字。再后来,小镇上修建了一个电影院,小广场上就再也没有放映过电影。
那些年的日子很贫困,但今天回想起来,却很快乐!
辛劳一生的父亲
沿着村东小路走10分钟,有一座火车小站,那是一幢米黄色的砖瓦平房。每天都会有几趟客车在这里经停,粗犷的汽笛声在几里外都听得到,父亲就在这座车站工作。儿时觉得他的工作很神气:站在站台上,手里分别拿着红色和绿色的旗子。客车进站时,他挥舞红旗,车就会慢慢停下来。等到乘客下车和上车后,他又挥舞绿色的旗子,列车会徐徐开动。车厢是草绿色的,车头是烧煤的蒸汽机车,硕大的前轮被染成红色,车顶的烟囱会脱出长长的烟柱。有时候火车两侧的气缸会喷出浓浓的蒸汽,发出巨大的声响,震耳欲聋。

记忆中,父亲在家的日子一直都在忙碌。他很喜欢在菜园中侍弄果蔬,那精细劲儿似乎是在进行艺术创作。我有时会拿起农具帮他打理,但很难达到父亲的要求。在屋前,他辟了两个小花圃,种下花草,又在园中种了十几棵果树。老屋西边有一个小池塘,父亲每年春天在里面撒些鱼苗,秋天里便会有一份收获。父亲还在园中种了三趟葡萄,秋天果实果实累累,色泽黝黑,又酸又甜。葡萄架之间栽上应季蔬菜,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草莓、香菜、葱蒜、白菜、土豆。有时候,父亲把新鲜蔬菜装到手推车里,运到八里外的一个集市卖掉,贴补家用。在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日子里,这些都是纯正的“绿色食品”。
儿时,母亲没有工作和收入,全靠父亲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。父母又是各自家里的长子和长女,两边都有些负担,生活很是拮据。为了省电,开关25瓦的电灯都很仔细。小学时,我生过一次大病,九死一生,此间父母遭受的煎熬无以言表。中学六年,我寄宿住校。学校里吃不饱,家里若有好吃的饭食,总要留到周末我回家才做,返校时再带上煮好的鸡蛋。父亲是农家子弟,本该在1959年参加高考,但由于家境贫苦,在高考前三个月,父亲不得不选择了退学,让我考上大学也是他最大的心愿。
盛夏傍晚,夕阳西下,一家人吃过晚饭,坐在院子里纳凉,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。我和妹妹一天天长大,父母仍喜欢回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,讲起过去生活困难的日子,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。这时妹妹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,体会着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天黑了,母亲去邻居家聊天,闲不住的父亲不知在屋里忙些什么。夏夜的风很凉爽,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气息,天空一轮弯月,耳边蛙声一片。我站在院中,凝视着夜空中繁星点点,那种明静的心情真想永远留驻。

►61岁的父亲站在院中
1995年春,我启程到江南大学攻读博士。正月初九的早上离家,母亲把我的东西收拾成两个大包裹。我取来扁担准备担起行囊,父亲忽然说了一句“让我来吧”。隆冬时节,寒风习习,地上覆盖着前夜下过的一场雪。一家人沿着村东小路向车站走去,父亲挑着行囊走在前面,坚实的脚步踩在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响声。我猛然发现父亲的脊背已经微驼。多少年了,父亲用这根扁担挑起家庭的重担,而今又挑起儿子远足的行囊。如同一根扁担,父亲一生都在承载责任和担当。
1997年夏,那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。临行时,父亲在站台上忽然说了一句“这次在家呆了四十一天,以后就没有暑假了”。列车徐徐驶出小站,父母依然一动不动的伫立在站台上。南望田野里的老屋,小路迤逶,炊烟袅袅,同乡愁一道飘散在秋风里。
常年在外,父母头上的白发也让游子心头况味四起。2004年,父母在纠结中卖掉了乡下的老屋,住进了城里的楼房。进城后,父亲还是经常念叨在乡下的日子。又过六年,父亲去世。因为不想触景伤怀,母亲也不愿意再回乡下的老屋——父亲和她曾在那里生活了整整35年。
最后一代农民
人生总在经历与追求中行进,工作以后我一直定居上海。繁华的都市里,人们行色匆匆、忙忙碌碌。有些朋友厌倦了雾霾和喧嚣,说到田园生活,就想起天然氧吧、青山绿水和高天流云,青翠欲滴,赏心悦目。然而,这只是旅行者的心态,锄禾日当午远非那么浪漫。打高尔夫和抡锄头,从动作上大同小异,但做起来却是咫尺千里。1966~1976年,在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的口号感召下,中国有过一千多万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,后来他们又纷纷带着青春的叹息返回城里。有些作家曾以这段经历写了很多知青小说,我很爱读。因为,那就是我们祖祖辈辈过的日子。

►1999年国庆假期回家,走在乡间小路上
2018年夏,我回老家参加中学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,又特地去了一次乡下的老屋。曾经的五户人家,只有一户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,人气凋零,一片破败。老屋已是残垣断壁,村口的老井早已废弃,羊肠小路蒿草丛生,那座火车小站几年前也停运弃用。空气中依然是熟悉的味道,我呆呆的站在田埂上,回忆少年时代,恍若隔世。
来到镇里,街巷很冷清。我找了一家饭馆,约了仍生活在乡下的亲友相聚。这两年粮价下跌,农民辛苦劳作,省吃俭用,一年种地的收入不过万元。经济形势不好,周边的零工活也不好找。然而,娶媳妇的开销已经涨到五十万,为此有些人家不得不东拆西借。下一代考上大学的很多,但考上名校的很少,寒门已难出贵子。孩子毕业后在城里买楼,父母继续省吃俭用,谋划着帮儿女还贷。一场小病,花销就得千八百元。养儿未必能防老,只能祈祷别生大病,小车不倒往前推。
工业化农场是大势所趋,延续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,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大都年过半百,已然是最后一代农民。听说靠近城区的有些村镇,政府征地后给了农民几十万补偿,很多人盼着自己的地将来也能被征用——尽管也知道这种事情遥遥无期。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,小人物的最终命运往往被忽略不计。
“遥远的夜空,有一个弯弯的月亮,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,小桥的旁边是那条弯弯的小河,弯弯的河水流啊,流过我的心上”。中秋月夜,又想起5000里外的故乡田野。故乡可以是一个省份、一个市县、一个村镇,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家,其实只是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,这里有过父母忙碌的身影。小时候,自己曾在黄昏的小路上等待父亲回家,在河边嬉水捉鱼,在田野中砍藤割草,在林间攀爬嬉戏。生于斯,长于斯,草木有情。都市的楼宇固然舒适明亮,然而对于离家的游子,故乡是永远的根。
(写于2018年9月24日中秋)
作者简介:崔凯,食品工程博士、心理学博士,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,财经图书、科普文章和散文作者。